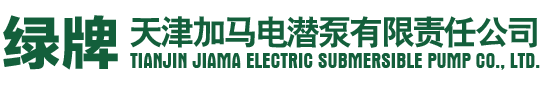防疫攻堅——細說試劑盒和抗病毒藥物研發(fā)中的化學反應
自新型冠狀病毒引發(fā)的肺炎疫情暴發(fā)以來,關于病毒檢測和治療方面的一些科學內容迅速引發(fā)關注。除了醫(yī)學相關的知識,最讓人牽掛的應該就是關于病毒檢測和抗病毒藥物方面的知識了。前者決定了患者是否能夠確診,后者意味著我們能否更加有效地治療疾病。在病毒檢測和抗病毒藥物方面,化學工業(yè)的相關技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,體現(xiàn)在藥理研究、分子設計、藥物合成等很多方面。
.jpg)
研發(fā)思路是阻斷病毒復制
在介紹病毒檢測和抗病毒藥物之前,我們首先來簡單的介紹我們的技術應用對象——病毒。
如果您完整接受了中學教育,您應該會對病毒有一個基本認識。病毒是由一個核酸分子與蛋白質構成的非細胞形態(tài),它們無法自行表現(xiàn)出生命現(xiàn)象,是介于生命體及非生命體之間的有機物種,既不是生物亦不是非生物。
病毒由兩到三個部分組成:所有病毒都含有遺傳物質——核酸(RNA或DNA),多數(shù)病毒有由蛋白質形成的衣殼,用來包裹和保護其中的遺傳物質。此外,部分病毒在到達細胞表面時能夠形成脂質包膜環(huán)繞在外,本次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-nCoV就是如此。病毒的形態(tài)各異,從簡單的螺旋和正二十面體到復合型結構均存在,顆粒大小大約是100納米左右。
我們知道,一切生物的遺傳信息都儲存在核酸上。對于一般的生物細胞,遺傳信息的表達是一個頗為復雜卻極度高效的生物化學過程。以真核細胞為例,儲存在DNA上的遺傳信息(表現(xiàn)為構成DNA的堿基對的特定排列方式)通過RNA轉錄,再由RNA轉譯,合成特定的蛋白質,從而得以進行特定的生命活動。而對于病毒來說,它必須借助侵入的特定細胞,利用這個細胞(稱為宿主細胞)的現(xiàn)有工具進行自身遺傳信息的復制和轉譯,從而繼續(xù)傳播。
相對于一般的真核細胞,病毒的遺傳信息十分簡單,但復制和轉譯方式多樣。對于病毒的檢測者來說,只要能夠將病毒從環(huán)境中分離出來,對其遺傳物質進行檢測,就可以判斷是何種病毒了,這是病毒檢測的思路。另外,如果我們能夠阻斷病毒的復制過程,我們就能阻斷病毒在體內的傳播,進而治療疾病,這是抗病毒藥物研發(fā)的思路。
.jpg)
病毒復制機制。(資料圖)
試劑盒需要聚合酶鏈式反應技術
關于本次2019-nCoV病毒檢測,如果您關注新聞,您可能會了解到試劑盒這個“神器”的存在。有了試劑盒,我們就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確診病例,如果試劑盒不夠用,整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確診都成問題。
不過,您有沒有思考過這么一個問題,試劑盒為什么能夠在短時間內發(fā)現(xiàn)病毒,從而確診呢?我們前面已經(jīng)提到,生物遺傳信息的表達方式十分復雜,速度也并不算很快。可是,傳染病的防治要求醫(yī)務工作者以最快的速度發(fā)現(xiàn)病例,并對確診患者進行隔離和治療,這個矛盾是如何解決的呢?
原來,目前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試劑盒,主要是利用RT-PCR技術,即Reverse Transcription-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。翻譯成中文,叫做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。聚合酶鏈式反應(PCR)技術是生物化學領域非常重要,且廣受認可的一項應用技術,而RT-PCR技術是PCR技術在RNA病毒檢測方面的衍生。
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PCR。在沒有PCR的時代,科學家是如何復制生物基因的呢?首先,將DNA經(jīng)限制酶剪裁,再利用連接酶加到運載體中,之后利用瞬間電擊或是熱休克的方式,送到大腸桿菌感受態(tài)細胞中,將此菌于培養(yǎng)皿大量繁殖培養(yǎng),再經(jīng)過繁復的分離、純化過程,時間通常需要近一周,才能大量復制片段。可以想象,如果使用這種方法確診傳染病會是什么結果。
1986年,美國生物化學家凱利·穆利斯發(fā)明了PCR,他也因此獲得了199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。穆利斯利用DNA聚合酶來擴增特定的DNA片段。在中學階段,我們就知道,DNA聚合酶天然存在于生物體內,當DNA開始復制時,解旋酶將雙股的DNA分開成兩個單股,DNA聚合酶便結合在兩DNA單股鏈上,生成互補鏈。在穆利斯最初的PCR中,他將雙鏈DNA加熱到96℃,使得雙鏈分離,再加入DNA聚合酶,以在生物體外獲得新的DNA鏈,但由于反應在高溫下進行,效率不高。后來,嗜熱細菌水生棲熱菌體內產(chǎn)生的DNA聚合酶的發(fā)現(xiàn),提高了PCR的效率。由于嗜熱細菌生活在溫度達到50℃~80℃的間歇泉中,其DNA聚合酶具有耐熱性。在用于PCR時,高溫并不能破壞這種DNA聚合酶,PCR由此變得簡單并且可以由機器操作,大大減小了核酸檢測的難度。不但如此,現(xiàn)在一些廠商利用蛋白質的模擬分析,將DNA聚合酶的結構進行人工修改,還可以合成出性能遠超原本自然提取而來的酶。
對于PCR來說,高效的DNA聚合酶和DNA模板是必需的,當然還有其他必需成分,如引物和緩沖劑。但對于2019-nCoV這樣的RNA病毒來說,我們復制的樣本并不是DNA而是RNA,這是就需要將RNA逆轉錄為互補DNA(cDNA),再進入DNA擴增。RT-PCR的指數(shù)擴增是一種很靈敏的技術,可以檢測很低拷貝數(shù)的RNA。目前,這個技術廣泛應用于疾病的診斷,除目前的2019-nCoV,還有艾滋病病毒、埃博拉病毒、流感病毒、丙肝病毒以及麻疹病毒等,都可以用RT-PCR進行檢測。
本次2019-nCoV病毒檢測,一般只需要4~6小時,即可對咽拭子樣本獲得比較準確的結果。目前,隨著相關企業(yè)的不斷研發(fā),已有1~2小時即可出結果的檢測試劑盒出現(xiàn)。不過,RT-PCR有一定的漏診情況,即使多次檢測,也可能會有假陰性結果出現(xiàn),需要注意。
.jpg)
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。(資料圖)
藥物研發(fā)依賴化學合成
除了檢測試劑,對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,人們更加關心的是如何從根本上治愈疾病。不過,截止到發(fā)稿時,還沒有官方發(fā)布的特效藥物出現(xiàn)。不過,由于醫(yī)學界已經(jīng)對RNA病毒的傳播和感染機制有所認識,目前,研究人員正在對現(xiàn)有抗病毒藥物進行篩選。
抗病毒藥物是藥物家族中非常重要的一支。我們知道,藥物與化學密不可分,目前市面上銷售的絕大部分西藥都是化學合成的,早期的藥物化學發(fā)展史幾乎等同于有機化學發(fā)展史,有機化學工業(yè)最初的產(chǎn)品幾乎都是藥物。隨著化學和醫(yī)學水平的不斷發(fā)展,藥物的結構越來越復雜,功能越來越明確。到上世紀40年代,抗生素的問世,使人類對于細菌這一病原體也有了強力藥物。不過,對于另外一個重要的病原體——病毒,抗病毒藥物的發(fā)展卻晚了一些。
抗病毒藥物是一類用于特異性治療病毒感染的藥物,類似于抗生素治療細菌感染一樣,特定的抗病毒藥物對特定的病毒起作用。但抗病毒藥物和抗生素不同的是,后者消滅細菌,前者只是抑制病毒的發(fā)展。它與我們在本系列科普中提到的消毒劑不同點在于,抗病毒藥物抑制體內的病毒,而后者是用于消滅體外的病毒。
抗病毒藥物的機理主要是通過影響干擾病毒復制周期的某個環(huán)節(jié)來實現(xiàn)抵抗病毒,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抑制或殺滅病毒、干擾病毒吸附、阻止病毒穿入細胞、抑制病毒生物合成、抑制病毒釋放或增強宿主抗病毒能力等。目前,市面上能看到的大多數(shù)的抗病毒藥物是用于對抗艾滋病毒、皰疹病毒、乙型肝炎病毒、丙型肝炎病毒、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等。
與發(fā)展超過70年的抗生素相比,抗病毒藥物還是個“晚輩”。但過去的40年間,抗病毒藥物的發(fā)展非常迅速。其中,艾滋病的不斷蔓延推動了對抗病毒藥物的需求,而抗艾滋病毒藥物阿昔洛韋的面世,成為了抗病毒藥物發(fā)展的里程碑。
上世紀70年代,艾滋病在世界上迅猛傳播。面對不斷蔓延的艾滋病疫情,化學家開始從核苷類似物尋找抗病毒的良藥。化學家發(fā)現(xiàn),當病毒復制時,核苷類似物可以被相關酶當作核苷并用于合成其基因組,而這些類似物缺少與磷相連能夠相互連接形成DNA骨架的羥基,會造成DNA的鏈終止,從而抑制病毒的增殖。阿昔洛韋問世。作為一種核苷類似物,它最大的特異功能就在于可以抑制病毒用于編碼的胸苷激酶和DNA聚合酶,能顯著地抑制感染細胞中病毒DNA的合成,而不影響非感染細胞的DNA復制。它的發(fā)明者,美國生物化學家格特魯?shù)?middot;埃利恩也因此獲得了198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(yī)學獎。正是在一代代生物化學家和醫(yī)學家的努力下,在得到妥善治療的前提下,艾滋病感染者的預期生存期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延長。根據(jù)估計,如果一個20歲的青年人在1996年患上艾滋病,他只能活到大約39歲。如果一個同樣的20歲青年在2011年患上艾滋病,他可以活到大約70歲。
目前,抗病毒藥物共有六大類,即穿入和脫殼抑制劑、DNA多聚酶抑制劑、逆轉錄酶抑制劑、蛋白質抑制劑、神經(jīng)氨酸酶抑制劑和廣譜抗病毒藥。
.jpg)
治療用藥正在試驗
在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(試行第五版)》中,在抗病毒治療方面,寫道:目前沒有確認有效的抗病毒治療方法。可試用α-干擾素霧化吸入(成人每次500萬U或相當劑量,加入滅菌注射用水2ml,每日2次)、洛匹那韋/利托那韋(200mg/50mg,每粒)每次2粒,每日2次,或可加用利巴韋林靜脈注射(成人每次500mg,每日2次)。要注意洛匹那韋/利托那韋相關腹瀉、惡心、嘔吐、肝功能損害等不良反應,同時要注意和其他藥物的相互作用。而據(jù)國家衛(wèi)計委透露,目前阿比多而和瑞德西韋也在進行試驗。下面,我們來簡要介紹一下阿比多爾、洛匹那韋/利托那韋和瑞德西韋三種藥物。
阿比多爾:阿比多爾是前蘇聯(lián)藥物化學研究中心研制的非核苷類抗病毒藥物,于1993年在俄羅斯首次上市,目前主要在俄羅斯和中國用于流感的治療。相對于常見抗流感藥物奧司他韋,阿比多爾合成簡單且廉價,而其抗流感病毒的臨床證據(jù)就相對不足。
這一次在新型冠狀病毒的治療中,我們在《武漢協(xié)和醫(yī)院處置2019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策略及說明》中也看到了它的身影,但目前并沒有確切的證據(jù)證明阿比多爾對于新型冠狀病毒的治療有效。武漢協(xié)和醫(yī)院的那份指南后來也漸漸被新的更好的方案替代。
洛匹那韋/利托那韋:洛匹那韋是一種新的抗HIV的蛋白酶類抑制藥物,主要通過阻斷Gag-Pol聚蛋白的分裂,產(chǎn)生未成熟的、無感染力的病毒顆粒而發(fā)揮抗HIV病毒的作用。LPV主要由肝細胞色素P450系統(tǒng)廣泛代謝,且?guī)缀鯇iT由CYP3A同工酶代謝。而利托那韋不僅是一種蛋白酶抑制劑,還是一個強效的CYP3A酶抑制劑,可抑制洛匹那韋在體內的藥物代謝,從而提高洛匹那韋在血漿中的藥物濃度,增強抗病毒作用。所以,臨床上通常是把洛匹那韋和低劑量利托那韋聯(lián)合使用,這種復方制劑,商品名叫克立芝,于2000年被美國FDA批準上市。本次疫情,這個藥首先被大眾所了解,是因為北大第一醫(yī)院呼吸和危重癥醫(yī)學科主任王廣發(fā)居家隔離時自稱用了這個藥進行治療最后痊愈,泰國的痊愈案例,很可能也是使用了克立芝。
這個藥一度給本次疫情帶來希望,但是目前沒有證據(jù)證明克立芝在臨床中有效,目前的報道都是零星的案例,不具備代表性。細胞學和動物學研究表明,克立芝的抗冠狀病毒作用和肺部保護能力不如瑞德西韋。
瑞德西韋:瑞德西韋是一個作用于“依賴RNA的RNA合成酶(RdRp)”的廣譜抗病毒藥物,是由吉利德開發(fā)的一種新型實驗性廣譜抗病毒藥物,用于治療埃博拉病毒。據(jù)近期的一項研究顯示,瑞德西韋和干擾素IFNb1-b的聯(lián)合用藥對MERS有顯著療效。目前,該藥正在進行臨床實驗。
不過,瑞德西韋的開發(fā)者吉利德公司也發(fā)表聲明說:瑞德西韋尚未在任何國家獲得批準上市,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也未被證實。
.jpg)
來源:中國化工報